《火与玫瑰》是葛兰西《1908年——1926年书信集》的中译本。译者为田时纲老师。在这些书信中,除了与亲人、爱人和朋友谈一些私人的事情之外,葛兰西还对他所经历的社会党的分裂、工人运动、与法西斯的斗争等当时的重大问题作了大量的讨论。由于这些书信写作时间正好是意大利共产党从萌芽(从社会党分裂出来)和发展的时期,因此对当前在各国,尤其是具有类似国情(农民仍然较多,专制)的国家致力于恢复和重建共产主义力量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先进工人来说,具有极其重大的参考价值。如下是我们从《火与玫瑰》中选取的若干与现实关系比较紧密的段落,希望能对读者有所帮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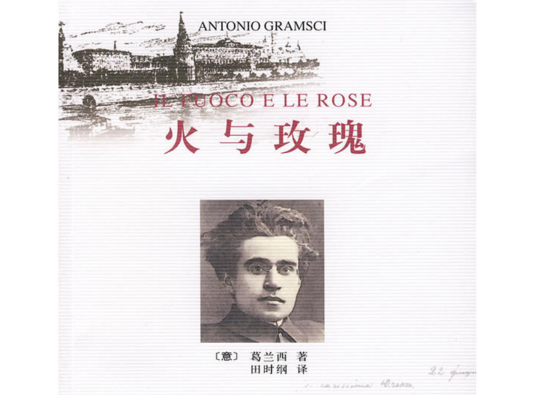
1 理论研究
“我们认为创建一个经济研究室十分有益,该研究室为党工作,并为党的斗争和党的知识准备吸收人才。研究室可以是合法的,并受党控制却没有入党的人员管理。研究室的目的可以是撰写劳动者阶级同资本家组织比较的国内国际形势(失业、工资、工会斗争、组织)的月报或半月报。应当小规模地从事与英国工党劳动研究部相同的工作。月报可以订阅,还可以为各种色彩的工会承包信息服务。可以考虑出版英国《Common Sense》(常识)式的政治内容半月刊,即以本质上共产主义观点研究工人阶级的国内和国际问题,但以客观形式显现的信息和公正无私讨论的刊物。”
“你们应当组织全国范围内提供党关于国家各方面总形势的报告。在每个方面都应有一位信息员。材料应根据行政区、管辖区或省加以集中,直至逐渐形成每月地区报告。”
——葛兰西致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23年,《火与玫瑰》第91页
2 干部培养
“1,缺少群众运动不可能促进青年的组织和文化的才能在文化圈之外发展。今天一位青年若不通过学习,能以哪些形式积极参加阶级生活并提高觉悟?显然,在反动时期会形成神秘主义的病态倾向,因为关系到我们的政权,我们必须坚决有力地与之斗争。2,我们的弱点总是在于缺少组织人才,不仅指高级人才,也包括中级和初级人才。在潜在和实际跟随我们的群众与我们的组织者之间不存在适当的力量关系,因此我们往往不得不放弃阵地,往往不得不丧失主动性。
“移民和屠杀恶化了这种形势,虽然在这一时期许多志士经受了考验,意志更加坚定。我以为,必须开展一次宣传运动以提高觉悟坚定意志,必须努力创建强大政党的干部队伍。我也曾想建议在国外建立党校,但为什么不在意大利也创办此类学校?
“即使在正常时期兴办此类内部学校也应该成为党的基本活动。必须在所有省培养党校教员,并就工人政治工作的一切方面给他们下达指示。为了无产阶级崛起时刻的到来,我们党需要至少3000名组织者,他们能胜任支部和工会等机构的书记职务。”
——葛兰西致艾尔库诺,1923年,《火与玫瑰》第107页
3 合法活动的重要性
“在意大利目前的形势下,党要特别注意团结广大工人群众的方法。如果党没有采取具有某种重要性的合法活动,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如下后果:
一,工人群众,因此也包括不认为脱离群众的党员们,受到由国家领导人通过所有形成舆论的机构发动的系统宣传运动的影响,这种运动旨在摧毁革命意识形态,鼓吹革命纲领已经失败,至少需要50年才能再次谈起它。最好的可能是这种运动能够造成消极状态,放弃直接革命工作,期待同流合污的工人政党通过组建民主集团政府重构革命力量能重新组织的自由环境。
二,这种精神状态在党的最负责任的中心的某些部分也有反映,能够产生彻头彻尾清算革命意识形态的派别。贝洛内对邦巴齐事件的有根据的解释也表明这种危险在党内已不再是一种假设,而是一种现实,党的形式造成不能正确评价其限度和深度。
三,直接站在我们运动右翼的政党和派别,由于统治艺术的原因能够保持合法地位,不可避免地自动地利用对它们有利的形势,用他们往往带点共产主义词句的文献夺取我们的报刊的传统读者。这个政党或派别的机关必将行使政治领导中心的政治职能,降低或完全去除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威信和权威力量,结果它对群众只能不定期地,不规则地证明自己的存在。”
——葛兰西致意共中央执委会,1924年,《火与玫瑰》第136页
4 统一战线
“在德国争夺领导权的两个集团都没有能力、不能胜任。所谓少数派(菲舍尔——马斯洛夫)无疑代表革命无产阶级多数,但它既不具有在德国进行胜利革命所需的组织力量,也没有坚定不移的方向以避免比十月更大的灾难。布兰德莱尔—塔赫伊梅尔集团在意识形态和革命准备上比前者更强大,但它自某些方面的弱点比前者更大、更有害。布兰德莱尔和塔赫伊梅尔变成革命的‘犹太教法典学者’。由于他们想不惜一切代价找到工人阶级的同盟军,结果最终忽视了工人阶级自身的作用;由于他们想争取被社会民主党人控制的工人贵族,他们相信能够不再实行工业性质的纲领,这一纲领基于共产委员会和监督,他们想要在民主阵地上同社会民主党人展开竞争,从而导致工农政府口号的蜕化。那么,哪个集团是右翼,哪个集团是左翼呢?问题有点错综复杂。”
——葛兰西致党内若干同志,1924年,《火与玫瑰》第163页
5 直接纲领
“齐尼原则上是共产主义者,但也在信中说自己已经老了、十分疲惫,对任何事、任何人都不再信任,除了从事自己的工作外,他致力于撰写一本书使其思想系统化,从信中包含的暗示可见,是政治消极状态的纯粹反映…为什么在1919年—1920年同我们在一起积极活动的知识分子今天普遍具有悲观主义和消极性的精神状态?我觉得,这是由于,至少部分地由于我们党缺乏一个直接纲领,这一纲领建立在目前形势允许的可能解决前景之上。我们拥护工农政府的口号,今天在意大利意味着什么?无人说得清楚,因为无人关心此事。广大群众(知识分子自动地成为其代表人物)没有明确的方向,不知道如何走出目前的窘境,因此就接受做一点努力的方案,接受改良主义的符合宪法的反抗解决方案…因此,我认为伟大的工作应当沿着这一方向进行:政治宣传工作和探索形势的经济基础的工作。我们应当提出目前形势能允许的所有解决方案,我们对每一个方案都要制定方针…立宪会议的口号重新可行吗?如果可能,我们将对它采取什么立场?可能设想从法西斯主义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吗?可能出现哪些中间阶段?我们应当从事这种政治考察工作,我们应当为自己从事这一工作,我们应当为党员群众和广大群众从事这一工作。”
——葛兰西致陶里亚蒂等人,1924年,《火与玫瑰》第206页
6 群众比知识分子更加坚定
“我发现群众不像知识分子那样悲观。群众在探寻一个路标、一个焦点,为群众指明方向,这是今天我国最重要的问题。老一代知识分子拥有许多历史经验,他们看到我国国民在最近几十年的曲折发展的全过程,但他们缺乏责任感和使命感,恰恰在这一危难阶段,他们畏首畏尾,不愿澄清、组织并集中业已存在的理想力量,这些力量无需鼓动(这点可能是乌托邦的),只需集中和指引。你看看期刊发生的事情,它今天的印量是1920年的两倍,这一迹象证明了我给您写的那些内容。在1920年,形势显得特别有利,那是一种四日热症般的狂热,今天对形势的认识更加深入、更加坚实、即使周围是一篇苍凉的景象。”
——葛兰西致齐诺·齐尼,1924年,《火与玫瑰》第226页
7 工人运动
“还是有许多事情要做:工人群众相对平静,孤立的罢工继续发生。如果我们彻底实行车间支部的组织原则,正如你同意的那样,如果我们召开工人大会,到一定程度,即使我们不想,我们也将面对必须进行真正意义的工会行动的形势…由于我们不想创建一个新工会中心,显然,组织应当是非法的。这不危险吗?毫无疑义。然而,如果我们想要工作,一般说来这不可避免。你相信广大群众对交换不同党派的工会委员会的信件很感兴趣吗?这只对委员会本身有用,对在不太艰难时期拥护党的少数工人有用,但丝毫不能影响广大群众。广大群众只能感受到由在广大群众中扎下根的组织采取的实际行动的作用。意大利工人阶级的主要弱点是什么?孤立、分散,我们应当同这种状态作斗争。显然,我们不可能渴望斗争立即生效。然而,我举个例证:假若我们已经拥有一个在工厂扎根的组织,通过方法得当、井井有条的宣传运动,肯定能在5月1日取得好的结果。仿佛在工人中形成信念:业已存在一个中心,在所有工厂进行相同工作,可以发起运动而每个工厂无需害怕被孤立从而被镇压?通过多种手段,在其总体上会产生预想的感觉。依我看,必须让我们的各个小组,以各个工厂的全体工人的名义,对目前局势的提案进行表决;然后我们的报刊刊登消息,工人们阅读报刊并了解情况。如此等等。我认为应当探寻全新的动员和宣传以及组织的技术。必须让大部分群众习惯于非法行动和保守秘密,等等。我觉得在这方面意大利工人因沉痛教训已取得了很大进步。以致在我看来,甚至应当提出这一问题:应在都灵、米兰和其他大城市组织一次公众游行示威。你会说,这太夸大其词了。我这样说一点不开玩笑。我认为在都灵和米兰,通过精心布置的组织工作,能够在城市某点集中5万工人,不会发生灾难,此事会产生巨大反响。当然,今天想干类似事情有点儿疯狂,但我说在从事上文提及的活动时,我们必须提出产生类似结果的问题…我们认为它们绝对不是乌托邦的,我们必须走出一潭死水。”
——葛兰西致乌尔巴尼,1924年,《火与玫瑰》第24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