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我们都知道梁启超是主张改良不要革命的。但社会上包括梁启超在内的少数人,其财富爆炸式的增长,这可跟磨磨蹭蹭的渐近改良不是一节奏啊,跟暴力革命倒是一节奏。我过去看民国老照片,发现老百姓全都黑不溜秋的,名符其实的“黎民”,我原来还以为是照相器材的原因呢,但再一对比同时代照片上的“民国范儿”如林徽因陆小曼徐志摩,一个个都挺白净的,看着跟绝大多数中国人分属俩人种似的。社会两极化成这样,革命不就是呼之欲出了么?
作者按: 这是我最近在解玺璋先生新著《君主立宪之殇》出版沙龙上的发言。两位朋友读后有所回应,我觉得很有意思,亦作为附录放在后面,以飨读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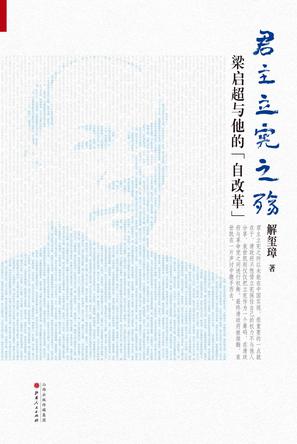 解玺璋:《君主立宪之殇——梁启超与他的“自改革”》,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4月版
解玺璋:《君主立宪之殇——梁启超与他的“自改革”》,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4月版
革命的前因后果
这本书我还没来得及看完,睡觉前躺床上翻了两三个晚上,不到三分之一。我想玺璋先生之所以写这部书,是因为近代史是中国当代何去何从的一个最重要的参照吧,总之是奔着今天来的。既然如此,那我就结合着中国的今天来聊聊这个话题。我对近代史不但没有专门的研究,阅读也非常有限,尽管社科院近代史所就在我家隔壁。
王焱先生刚才谈了政治史和思想史的区别,强调不要把政治史化约为思想史,这我非常同意。我就从社会或阶级的角度谈些肤浅的感想。
今天解先生和我们大家坐在这儿谈作为思想家、政治家、学问家的梁启超,从上世纪初到80年代大家也都是这样谈论梁启超的。但90年代、2000年以来社会上对梁启超似乎还有另外一种间接的谈法,那就是谈这位近代名人的著名儿媳妇林徽因,谈她主持的著名沙龙,沙龙里进进出出的著名男人,总之,谈的是一种“贵族”人生的样板。当代中国产生对“贵族”的需求,大概是从90年代中期开始的,社会沿着“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路线一路走来,开始了两极分化。一部分人富起来了,富起来后一方面要上层次,也就是讲究,甩掉“大金镏子”、“农民企业家”之类的粗放形象;另一方面就是希望长宜子孙、天长地久,到手的东西“神圣不可侵犯”。这两方面的诉求“贵族”这个词都准确地包含了。于是政治保守主义一路走高;于是《格调》、《上海的风花雪夜》、《上海的金枝玉叶》、《最后的贵族》、《张氏姐妹》、《民国四公子》、《红色贵族》等书风行一时,快成“贵族”的和想成“贵族”的人手一本照着勤学苦练。梁家的“贵族”沙龙就是在这种社会大背景下修葺一新,在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重新立起来的。
梁家“贵族”生活的奠基人当然是梁启超了。梁启超的上辈可不是什么“贵族”,80年代出版毛主席岳父杨昌济的日记,其中某日就有用梁任公也是农家子弟的例子勉励“毛生”自强不息的内容。估计梁任公父辈也就是个小地主吧,这个我没查过,但肯定不是世家。去年秋天朋友邀我去天津,说有梁启超和李叔同的故居,我说咱哪儿都不去就去这俩地方吧。梁启超故居有两栋西式洋楼,最先只有一栋,是辛亥革命后两三年盖的,后来又加盖了一栋读书写作的,即所谓的“饮冰室”。梁启超不是商人也不是职业政客,我相信他的怀抱志向也尽在苍生和学问。但这样的豪宅还是让我了一惊,我想它对于近代思想史以及近代社会史都是有参考价值的:财富向一部分人集中的速度怎么这么快呢?
我们都知道梁启超是主张改良不要革命的。但社会上包括梁启超在内的少数人,其财富爆炸式的增长,这可跟磨磨蹭蹭的渐近改良不是一节奏啊,跟暴力革命倒是一节奏。我过去看民国老照片,发现老百姓全都黑不溜秋的,名符其实的“黎民”,我原来还以为是照相器材的原因呢,但再一对比同时代照片上的“民国范儿”如林徽因陆小曼徐志摩,一个个都挺白净的,看着跟绝大多数中国人分属俩人种似的。社会两极化成这样,革命不就是呼之欲出了么?
刚才主持人介绍我是剧作家,“家”谈不上,但我的确写过几个剧本,其中《切•格瓦拉》最后一句是:“我在想,革命是不朽的。”其实我也经常在想,怎么才能避免革命。我希望能为革命釜底抽薪,而不为革命扬汤止沸。解先生这本书讲的是辛亥革命之前的那一段,他为中国错过立宪改良、走向辛亥革命而惋惜。其实,很难说立宪改良没成功,也很难说辛亥革命就是革命。在我看,辛亥革命就是立宪改良的成功。武昌这边炮一响,北京那边袁世凯冲紫禁城的孤儿寡母一皱眉头,不就基本上“和平转型”了么?全国没乱多少天,人也没死多少个,虽然“虚君共和”没戏了,但对皇室的优待写进了约法,民国的阁员接长不短进宫给逊帝下跪请安,遗老遗少在上海天津的租界里文酒风流,日子过得相当不错,这能叫革命么?应该叫非典型改良吧。问题不在于辛亥革命断送了宪政改良。问题在于宪政改良完成之后又发生了革命——从1927到1949年的大革命。这场革命有很多内外原因,但一个非常重要的内部原因是社会资源的分配太不平均了。记得80年代翻阅丁文江编撰的《梁任公年谱长编》,1927年南方农民运动轰轰烈烈,梁启超给他孩子的信里说,这是流民(游民)在闹事。
刚才王焱先生说了一个观点:中国没有地主。对此我有一点不同意见。王先生可能是说中国并非阶级分化多大的社会。这要看怎么说了。自周秦之变以来,中国的社会流动的确比较快,财主不三代,穷人不到头。很多人,包括梁漱溟和早期毛泽东,都持这种观点。但阶级固化的程度不高,不等于阶级分化的程度不高,循环的速度快些而已。每到大灾大荒之年,豪强大量购进土地,大批自耕农沦为佃农流民游民,这些无地农民小则打家劫舍,大则起义造反。前几年我到四川大邑参观刘文彩的宅子,太奢华太讲究了,完全可以成为当今土豪“上层次”的样板房。院里有些楹联,把“既富且贵且寿”的主人姬妾成群的生活描写的十分到位,我用手机拍了下来:“花泉成园,喜燕小莺娇,红杏枝头春意闹;神仙有窟,看云迷月澹,蓝桥路指密情深。”最近党中央提出要大力发展“乡愁”,任志强他们积极建言献策说,想要“乡愁”,那得有乡绅!我这算是为任老板他们提供点乡绅的信息,等土地都流转到他们手里后好一招一式地落实。
刘文彩家财富积累速度也是爆炸式的,“风雷起家业”(他家楹联),一代人之间就兼并了几十万亩土地。靠什么,院里还有条楹联说得明白:“大展经纶,由商而政而军,扶摇直上”——这简直是刘汉刘总和谷俊山将军的人生轨二合一。他一家几十万亩土地,那么得有多少家自耕农沦为佃农、流民或游民,一加减乘除,数不就是出来了么。梁启超先生当年正确地指出了革命的社会基础是流民(游民),可惜他没接着指出流民的主要成因在于两极分化的社会结构。这样的社会结构而不爆发革命,那只可能是蜜蜂等畜类的社会结构,不可能是人类的社会结构。今天很多人一方面穷奢极欲,争当革命的病因;另一方面又对革命的病状愁眉苦脸,赖这个赖那个,实在是可笑。更可笑的是他们认为革命之所以发生,是由于一大群傻子遇上了一小撮骗子或疯子。也许那几位真是骗子疯子,但问题是那一大群傻子为什么跟疯子傻子走而不跟你走呢?再说了,谁比谁傻呀,无论是“打下榆林城,一人一个女学生”,还是“分田分地真忙”,解决的都是食、色这样的基本人生需求,不糊涂啊。
我非常希望中国能够以改良而不是革命的方式完成社会政治治理的现代转型。但革不革命,不取决于你希不希望,而取决于社会分化到什么地步。我承认,人是希望社会分化的,希望自己出人头地,挣得比别人多、混得比别人好,这的确是人性。但不希望比别人挣得少,不希望比别人混得差,这也是人性,是同一人性硬币的另一面。1980年代大家都觉得自己很有可能在社会分化中胜出,于是人性的这一面通行无阻。但90年代尤其是2000年以后社会分化得几家欢乐几家愁,分化得后面追上前面、下面替换上面的社会流动渠道越来越不畅通,阶级和利益关系出现了垄断即固定化、封建化的趋势。这样一来,人性的另一面要便大行其道了:凭什么好处都被你们哥几个得了,凭什么钱都被你们姐几个捞了呀,而且还富二代、官二代、星二代、拆二代的要没玩没了?!竞争导致分化,分化走向垄断,垄断终结竞争,这是社会兴衰循环的常轨。走到第三阶段,社会就变得腐朽,失去公平,花光了合法性,就又需要改良甚至革命了。中国的革命,不妨从社会和阶级的角度想想它的前因后果。就说这些。
【经本人审定,在原录音稿基础上有所增损】
附录一:友人双石来信
至于有人说中国没有地主,那得瞅屁股坐在啥地方。立论者无非就是祭起了“江南无地主”的翻版,无非就是想说民国那会儿阶级分化没那么严重,土地兼并没那么严重。先不说说得对不对,民国那种发展趋势是不是朝着严重在走甚至在飞跑?当年沙龙中的大小布尔乔亚们,有没有什么非革命的办法对应对这种趋势?如果有,效果如何?在这种趋势之下,怎么完成宪政这个大课题?或者说宪政怎么应对这个大趋势,他们有过什么行之而有效的办法?站在人性高度作傲岸批评总是很容易的。解决社会矛盾无非就是两种办法,一是缓和,建立足够的权威(或者说宪政吧)有效遏止、节制矛盾各方利益的碰撞,一种就是干脆抽去矛盾各方的基础,再造新型的社会关系。应该说,这种社会性的实验迄今也没有扯出个子丑寅卯来,还是公婆两说。但一旦有一方节制不了没法节制,大多数人的利益不断地被碰撞乃至侵吞,那么第一种办法显然就无效,第二种办法也就成了没得选择的选择。真到了那般光景,不知那些想竭力以宪政之名想固化现有社会关系的大小布尔乔亚们,又该如何是好?
再给你贡献一个民国大佬陈长官辞修关于民国土地问题的东东,很生猛的——比“土鳖”共党的还生猛。陈诚回忆录中的,国内有版。
陈长官的结论是无可奈何的,没有非革命的良方。当然有人可以拿台湾和平土改来说事儿,可那是百万“果军”枪杆子下完成的(后遗症还多多),而民国迁台后与台湾土地主没有利益和感情联系的情况下,以大陆带过去的黄金作储备搞土地债券整成的,这套办法在大陆是整不成的。
陈长官勇于正视事实,这一点在民国诸大佬中凤毛麟角,令人感佩!然陈长官给出的办法,却不敢恭维啊!这一点,一民国范儿吕思勉老先生说极其精彩到位:天下有天良发现之个人,绝无天良发现之阶级;天下有自觉觉悟之个人,绝无自觉觉悟之阶级。
补充一下,陈长官的办法是说服教育地主——精神万能,道德说教万能,但陈长官自己心里明白,还不说土改,光是减租一项,他在湖北一域整成了几何?
陈诚谈民国土地问题
研究中国历代的乱源,其说聚讼不一;但农民无以为生,有揭竿而起者,群起响应,因而造成变乱,却是众说中最有力的一说。所以历代老成谋国者,无不着眼于土地问题的解决。孟子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可能是对此问题最有先见的名论。
秦汉以降,解决土地问题的谋画,多一时治标之计,日久弊生,乱亦随之;真正根本解决的办法,无疑的,还是要归之于国父“耕者有其田”这一伟大的号召。不过在中国几千年积重难返的封建社会之下,“耕者有其田”的目的,未可一蹴而就;因此国父才又提出“平均地权”的办法,以为逐步实现的张本。而实施“平均地权”的先期工作,就是“减租”。
民生主义第三讲中有一段话:“中国的粮食生产,既然是靠农民,中国的农民,可是艰辛而勤劳,所以要增加粮食的生产,便要在政治上、法律上制出各种规定来保护农民。中国的人口,农民是占大多数,至少有八、九成。但是他们由艰辛勤劳得来的粮食,被地主夺去大半,自己得到手的,几乎不能自养,这是很不平的。”这段话除去证明了上面“乱源”之说为不诬外,很明显地看出国父是以减租为保护农民利益的一个步骤。
中国人口之中占八、九成是农民,而在这八、九成农民之中又占七、八成是佃农。佃农就是“耕者无其田”而以佃种地主土地为生的农民。“耕者无其田”已然够“不平”的了,若再横受地主的压榨,以至“不能自养”,天下痛心疾首的事,还有比这个更厉害的吗?
当然,好的地主也是有的,但大多数是以佃农的血汗来营求自身安乐的剥削者。佃农终岁辛勤所得,要大半年送到地主的家里去,幸遇丰年,或者勉强还可以过活;而靠天吃饭的中国农村,水旱成灾是常事。这就无怪孟子说:“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了。
所以要拯救贫苦的农民大众,最简捷的办法就是减租。本党为遵行国父遗教,早在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一月于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即有“规定最高租额及最低谷价”的决议。同年十月举行中央与各省区代表联席会议,并决议以“减轻佃农佃租百分之二十五”为本党政纲,此后“二五减租”就成了国民政府的政策。不过因为国家多难,内忧外患,迄无已时,始终无法付诸实施。抗战军兴以后,“兵”、“食”之源,都要取给于农村。农民的痛苦未除,而负担反而愈益加重了,这与安定后方争取胜利的要求,实在大相违背。因此我想:越是在抗战紧要关头,需要解决土地问题越迫切;从前不能做的事,现在不能不做也非做不可。
湖北省在我尚未复职以前,已办理过一次减租,因为阻碍太多了,未能推行尽利。我到省以后,正拟旧案重提,适值鄂西一带二十八(一九三九)、二十九(一九四○)两年连遭旱灾,心中异常焦灼,乃发动各厅处人员及地方团队,替人民车水灌田。照理这该是农民欢天喜地的事了,不想农民对于此举的表现十分冷淡,只是未公然拒绝而已。始而我们觉得很奇怪,经过仔细考查之后,才晓得当地农民的土地,都为地主所有,正粮的收获,悉数交租,只有杂粮的收获,才归佃农;佃农交租时,地主请吃一顿饭,这就是辛苦耕耘的报酬了。农民种稻既然辛苦而无所得,所以宁愿稻子早一点枯死,反可提前播种杂粮。如此说来,他们不欢迎我们的车水运动,可谓理之当然。
太不公平的租佃制度,足可使农业减产,这道理本甚浅显,人人耳熟能详;但从这一次车水运动中,更加深了我对于此种制度的痛苦印象。这使我坚决地认定:纵然“耕者有其田”的遗教,一时不克实现,但“减租”的政策,必须贯彻施行,而且刻不容缓。
我们于三十年四月制定“湖北省减租实施办法”,提经省府会议通过实行。此项办法对于减租的原则以及推行方法、步骤等,都有详明规定。兹举其要点如后:
确定“二五减租”的内容:
农民佃租定为正产物总收获量千分之三百七十五:即由总收获量先提二成五归佃,所余七成五由主、佃对分。
原定佃租超过千分之三百七十五者,应减为千分之三百七十五;原定佃租不及千分之三百七十五者,仍照原约定。
确保农民利益并防止地主之巧取豪夺:
正产物总收获量如因佃农改良耕作而有增加时,仍依承租时总收获量缴租。农地因不可抗力致正产物歉收时,仍依当地习惯协议减纳;但正产物之总收获量不及三成者,概免纳租。
实施减租后,地主不得因减租而撤佃。
地主如有用压迫或欺骗手段,诱使佃农私相妥协,于减租额外另行私立租额者,一经查觉或被人告发,得由政府将原租土地免租三年,仍发交原佃农耕种。其情节重大者,并得依惩治土豪劣绅条例惩治。
规定推行步骤:
按年分区推行,其分区推行次序及办竣期限,由省府以命令规定之,期于五年内,次第完成。
办理减租地区,由区乡公所或联保办公处办理调查事宜,限定地主及佃农于定期内呈报农地面积、地点,正产物种类及常年收获量,原佃租额及押金数目等。地主不于限期内呈报,佃农单独呈报,具有同等效力。
为调解地主及佃户发生争执起见,省府并颁布“湖北省各县减租调解委员会组织规则”,规定各县成立调解委员会负责处理减租纠纷。
此外,省府为减租新政推行尽利起见,并决定加强督导及考核工作。规定由省府及专署派遣督导员,县府派遣指导员出发各地指导,同时并训练青年学生分赴各地协同推进;以期督促各级干部公平执行,倡导民众自动遵从命令。又,为加强工作效率起见,规定推行减租人员奖惩办法,以别殿最,而戒玩忽。
依照上述办法,即从三十年(一九四一)四月起开始实施,规定五年完成。第一年办理恩施全县各乡镇及巴东、建始、鹤峰、宣恩、利川、来凤、咸丰等七县各一乡镇,共计三十九乡镇,四百八十七保。第二年即三十一年(一九四二)度,办理郧西、郧县、均县、房县、竹山、竹溪等六县,及来凤、宣恩、利川、巴东、建始、咸丰、鹤峰等七县未办的各乡镇;共计二百三十七乡镇,三千三百三十一保。第三年即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度,办理石首、公安、松滋、枣阳、襄阳、宜城、光化、谷城、保康、南漳、宜都、兴山、秭归、长阳、五峰等十五县;共计三百五十一乡镇,六千一百四十三保(公安、石首、松滋、五峰、宜都、长阳等六县,后因战事影响,呈准缓办)。第四年即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度,办理英山、罗田、远安、长阳、五峰、宜都等六县,及宜城、枣阳、襄阳等二十六县未办的各乡镇。因于是年七月,我已奉准辞职,办理情形如何,已不得其详;至于第五年是后任的事,更不是这里所能报导的了。
现在应当检讨一下这三年多减租的成效。我们承认推行这项政策,是十分吃力的,并且也不敢保证每一个佃户都已得到减租的利益。原因何在?归总起来说,就是农村潜在的封建势力太大,有非一朝一夕所能铲除净尽的缘故。一般愚昧无知的佃农,久处地主高压之下,早就养成等于主奴的关系,他们不但听受地主的拨弄,并且还有口不由衷地表示信仰。政府的法令和地主的意旨,如果听凭他们的衡鉴,往往认为后者较前者尤为重要。这与政府威信的堕落,自不无关系。而豪绅地主盘据乡里,根深蒂固,一般农民只有承望他们的颜色,与之分庭抗礼,简直不是他们想象得到的事,此种事实关系尤为重大。以故减租政令不免有遭受破坏的地方。诸如:
地主有暗地指使佃户增加田亩数字或正产物的常年收获量,或将一部分田亩匿不陈报,以图抵补减租损失者。
地主任凭佃户单独陈报田亩及正产物收获量,但佃户在地主积威之下,仍多方维持地主利益,不敢有所短失者。
减租后,地主有不论年成丰歉,迫令佃户缴足法定租额者。
地主于佃户请示送租地点时,往往假词威吓,使佃户不敢依照规定减租,致有寅夜送缴免使人知者。
以上情形,均可见地主势力之大,竟可迫使无知乡农自动地放弃其应得的权益。
不过乡农不都是这样愚昧的,地主中也未尝没有开明识大体者。像何雪竹(成浚)、罗贡华两先生,都是湖北的大地主,都能率先
领导减租,以身为教,此种精神,至堪钦佩。更兼督导工作认真执行,宣传工作渐能普遍深入,减租政策还是收到了不小的效果。三十二年七月二十七日,重庆《新蜀报》曾刊载了一篇访问湖北的报导,其中有一段提到减租的事说:
当后方各地土地兼并与土地投机成为风气的时候,记者踏进一个农地租佃纠纷较少、土地问题比较合理解决的地区,感到特别新颖。近年来,各地主阶层操纵粮价,得到意外的成功。对于佃农们任意加租、任意加押,加租、加押不成,便任意撤佃,弄得耕者无利可获,只造成若干大地主的兼并。这种情况是可忧的。
在鄂西,我们今年也看到碧绿葱笼的稻田,但听说地主对兼并土地却并不感到兴趣,而相反的,大批佃农现在纷纷购地。“中农”恩施分行,在恩施、咸丰二县,半年内放出二百万元土地借款,大都是借给佃农购地的。而经他们统计的结果,在最近二年间,恩施、咸丰的佃农已有百分之四十变为自耕农。因为粮价增高,耕地的利益有保障,鄂西贫瘠的山坡荒地上便一块一块的变为绿田。增产有了显著的成绩,一般人认为这是减租政策的成功,……诚然不是过分的估计。鄂西改革土地的风气是造成了,地主大致知道什么是民生主义,而且知道政府是在实行民生主义。
恩施是当时省府的所在地,咸丰是与恩施接壤的县分,减租才特别着有较好的成绩,偏远的县分未必都能和这两县等量齐观,这是无可讳言的。不过我总觉得对于减租政策能够有正确的认识,有实施的决心,再能坚持到底,不为恶势力的阻挠所软化,则成果必能更为扩大,终于使农民普被其泽,也并不一定就是难事。
我这种乐观的看法,最基本的根据就是认定地主也是具有理性的人。在理性的启发之下,人人可与为善。让地主们了然于农民在走头无路之际是会造反的,中共就在这种夹缝中间成长起来,则他们自会选择:是接受减租政策好呢?还是等候受中共的荼毒好?再则农民怠耕的结果,足可使租佃双方两败俱伤﹙车水一事,可为明证﹚;那么地主们也就没有理由宁愿不减租之两败俱伤,而不愿意接受两利的减租政策。至于榨取别人血汗以营求自身安乐的生活,是不名誉、不道德的,并且还是可以贻祸子孙的,这种观念如能建立,则地主阶级欣然接受减租,将有“如水就下”、“水到渠成”之功效。所以我认为减租政策之未能普遍推行,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为不为”的问题。
附录二:友人曹豫生来信
看了你的文章,我虽不是学者,也没真正思考过这些问题,但也想说几句。前几年发生通钢事件后,我曾写了一篇文章,文章的最后一段是:当年,夏衍在《包身工》中,警告“当心呻吟着的那些锭子上的冤魂!”今天,我想到黑砖窑里的残疾人,小说《那儿》中的舅舅,南方冰冷机器上的断指,我想说:当心啊!当心革命的到来,革命的到来不是取决于你们“告别革命”的曲子唱得如何好听,它取决于你们做了些什么。
看来我早就同意纪苏老师的观点了。
时过境迁,中国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前三十年,“革命”的正当性不亚于今天的“民主”,是人人追捧并想贴在自己头上的词,而今天,“革命”恐怕都快与“专制”一类的词为伍了,而“民主”这个词却享有了“革命”一词昔日的荣光。中国的主流知识分子关于“革命”的主旋律论述是“告别革命”,对“革命”的批判,攻击甚至谩骂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是网络文化人的政治正确,其中也包括不少实际处于社会较为底层的网民。
但在我看来,对于革命的正经的批判有两个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好,其一是大力渲染革命的恐怖与暴力,却基本不提反革命的恐怖与暴力,这让很多人对革命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如数家珍,却不知道反革命的种种问题。这和前三十年是一个有趣的对照,前三十年我们都知道反革命的凶残和暴力,却不认为革命有什么问题。所以,当今天的很多人指责过去的历史如历史教材如何不可信,但是看了他们“还原真相”的历史后,却发现他们和他们指控的对象并无本质区别,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洋人在中国杀人,是为了传播文明,而中国人反抗洋人,则是因为喝狼奶长大的;洋人抢夺中国的宝物,则要感谢洋人替我们保存了宝物,这样的“还原真相”,恐怕也就骗骗那些网络傻瓜了。
关于革命的第二没解决好的问题是革命的成因问题。也就是纪苏老师说的“由于一大群傻子遇上了几个骗子或疯子”,这个解释极度欠缺说服力。当年我就疑惑既然那些地主,那些士绅被今天文人们说得那么好,一个个跟待宰的洁白羔羊似得,为什么普通民众,尤其是农民非要革命?要知道革命不是儿戏,是提着脑袋干的事,那么多的普通民众,放着那么“好”的日子不过,要跟自己的脑袋过不去吗?这说得通吗?要说有那么几个傻的是可信的,要说那么多都傻的不要命,怕是难以服人。就说今天,那么多公知和粉丝把今天的社会说得无比的黑暗,好像多数也是耍耍嘴皮子,像过去那样豁出去革命的也没见几个。就是通钢这样的事件,停止和民营合作后,也不再闹了,也没有要革命的意思。可见,革命不是社会矛盾激化到极端的地步,也是很难搞起来的。
还有一个批判革命的常见说法,那就是“革命之后”的问题,就是革命了半天,最后还是和革命前一样,革命者成了新上层而已,所以,还是要“告别革命”。这种说法也是有问题的。首先,“革命之后”和“革命之前”还是有区别的。就说中国历史上,这里把改朝换代也称为“革命”,新的朝代成立早期,很多时候往往民众的日子要比旧朝代后期好过得多,比如唐代对隋代而言,宋对五代十国而言,明对元而言等等,当然这些新朝代后来会变得和老朝代一样,就会有新的“革命”来修正它。如果没有这样的革命,老百姓的日子就苦得没边了。还有一点,很显然,革命很难解决社会分层的问题,就像有人说无非是革命者成了新“皇上”的问题,但革命以一种最剧烈的方式解决了社会各层上下流动的问题。即使现在的网络上,知识分子不是老是指责社会层级固化的问题,认为能上能下的流动才是健康的,批判现在出现的上层“二代”和下层“二代”的现象。当社会层级固化难以撼动的时候,革命无疑是一个最快的解决办法。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无疑解决了社会上下流动的问题,他还想解决社会分层的问题,结果失败了。以毛的能力尚不能解决此问题,以后我只相信革命解决社会层级流动的问题,不相信革命解决社会分层的问题。公平是我最重要的价值观,但是我知道社会不会有真正的绝对的公平,只有相对的公平,社会分层的现实其实告诉了我们这一点。
在当下的社会里,革命还有非常有趣的一点,就是让官方和知识分子非常地纠结。对知识分子而言,他们高声调地宣布告别革命了,但是其实只是自己告别革命了,骨子里却希望民众积极地革命,他们羡慕阿拉伯之春,羡慕颜色革命,抱怨中国民众是“圈养”的,不起来反抗他们所说的专制政权,也就是说,他们反对的是“革命”这个词汇,也为自己的不行动有了借口,心底里却希望民众去革命,去替他们实现他们的理想,这和当年闹革命的共党完全不一样。你说今天嚷嚷着告别革命的家伙,到底要不要革命?
为革命纠结的另一个是今天的执政党。我们的党其实是支持知识分子引吭高歌告别革命的,原因在于党的位置变了,当年是革命者,今天是执政者,今天要革命,那还能革谁的命呢?所以在党的支持下,告别革命的曲儿唱得格外动听。但是共产党又怕把革命完全否定了,原因就在于党承认自己犯了很多错误,但是党可以改正错误,比如文革后的拨乱反正,所以党是有执政合法性的。但是如果完全否定革命,那就不是共产党犯了错误了,而是党本身就是个错误,因为这个党实际上产生于革命愿景中。因此,党要掌握好革命与告别革命之间的度,关键在于这个度实在不好把握,因此就会纠结。
其实,我这里承认革命是正当合法的,不是为了促进革命,恰恰和纪苏老师一样,是为了用正确的方法防治革命的发生。仅仅是知识分子嚷嚷“告别革命”,屁用不顶。要真正地追求共同富裕,当然也只是相对的。要用更公平和公正防止革命的爆发。
